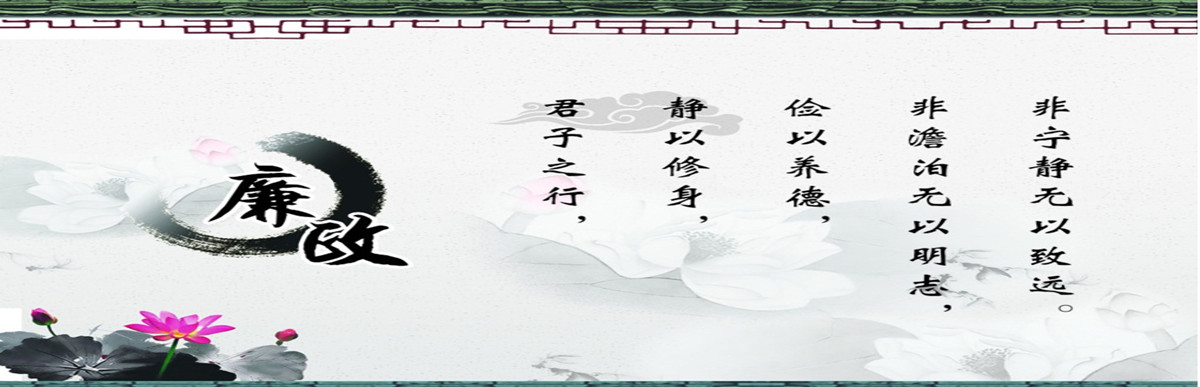革命不是入股分红
作者:时间:2015/03/25 00:00:00浏览: 次
一
“革命可不能有入股分红的潜在思想。”这是原中央监委(中央纪委前身)副书记钱瑛曾说过的一句话。不久前我在翻阅史料时偶然读到,顿时眼前一亮,感到饶有深意,发人深省。
此话出自一位省级地下党负责人的回忆。解放战争后期,钱瑛领导下的一个省级地下党组织连续三次发动武装暴动都失败了,负责人极为自责和苦恼,赴香港向钱瑛汇报,以寻求指示。不料这位一向为钱瑛器重的负责人,却在香港受到长达一个月鞭辟入里、深透骨髓的批评教育和整风学习,经历了人生中一次透彻的灵魂洗礼。事隔多年,这位负责人在回忆录中依然能很仔细地描述当年的场景:
“钱大姐还是那个老习惯,只是让你汇报,她一支接着一支地抽香烟,把眼睛眯起来,专心一意地听你讲,她不记笔记,也不插一句话,除非是有些情况她要你再详细补充,要形象和数字,以至一些我们认为毫不重要的细节,抓住问个不完。汇报听完了,她也不马上分析或回答问题,她叫你放开来休息两天,她再来谈。”
过两天钱瑛来了,在一般性地肯定地下党坚持工作的成绩后,她毫不客气地开始了暴风骤雨似的批评。她严厉地说:“一次失败了,你们再搞一次,再一次失败了,你们还要来一次?”“是什么思想使你们老撞南墙,死不回头?” 钱瑛认为他们之所以失败是拿自己有限的力量去和敌人拼命,对武装暴动目的认识不清,看不清白区武装斗争是配合解放区战场、地下党的存在就是胜利的道理;进而更尖锐地指出:“上升到世界观的高度……你们无外乎是想自己打出一个江山来,拉起一支队伍来,以便解放后,论功行赏,排班坐交椅吧?”
这位负责人是我十分敬重的一位革命者。当时钱瑛的指责听得他简直流泪,感到十分委屈,他说:“我们哪里想争坐什么交椅?我自己早就下定决心去掉脑袋的嘛。”
整整一个月,钱瑛和他激烈争论,严厉地批判、苦口婆心地开导,举了好多事例,说明不切实际的愿望却带来亡党掉头的教训。最后,她语重心长地说:“革命可不能有入股分红的潜在思想啊。”地下党负责人从难以接受,到逐步折服,最终心悦诚服。
革命者为革命成功当然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但是党的历史经验和现实教训都再再说明,每当革命如日中天、临近胜利之日,也是党内各种不良风气开始滋生之时。当时,钱瑛领导的地下党系统,就有个别干部不顾客观形势强拉队伍、冲动蛮干、甚或拼命捞政治资本以图论功请赏的情形,以致出现因判断失误、策略不当、纪律涣散而最终使党组织遭遇大破坏的严重事件,给党和革命事业造成极大的损失。钱瑛之所以不惜用宝贵的一个月时间对这位负责人进行专门的批评教育,目的就是要让他彻底明白错误根源,警惕和杜绝临近胜利之时党组织中可能滋生的“入股分红”的不良思想倾向。
这位地下党负责人不是唯一受到钱瑛批评教育的人。从1948年4月起,钱瑛将自己所领导的各省区党组织负责人和学运骨干分期分批地调到香港,进行严格的整风学习和教育培训。为此,她亲自制定培训计划,亲自讲课,仔细摸清每个人的情况,针对他们思想上存在的问题进行逐个谈话,告诫他们革命的目的是为了求得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是为劳苦大众谋福祉,作为共产党员谋事做事都必须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绝不能滋生“入股分红”的意识。
这是相当数量的一批干部,也是相当巨大的工作量。在革命即将胜利的时候,钱瑛的工作可以说是千头万绪,无比繁重。然而为了这群骨干分子的健康成长,她却能花费大量的精力来做培训工作。这样做的效果是相当可观的,这批干部接受整风学习后,被派往各地,也把她“革命不是入股分红”的理念带到各自的岗位。他们中绝大多数人解放后担负了各级党和政府机构的重要领导职务,其中还有不少省部级干部,他们都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各自的贡献。他们回忆起这段经历时的一个共同感受是:这是他们人生中一次极其重要和及时的整风,当年他们虽然被钱大姐整得很“痛”,但最终都能心情舒畅,轻装前进,并且受用终生。
二
钱瑛要求下属不能有“入股分红”的意识,她自己更是严格自律、身体力行地将之融入革命人生的各个方面。
“革命不是入股分红”,反映在革命意志上,就是立场坚定,勇于献身。钱瑛是1927年初入党的,当时正值党的事业烈火烹油之时,可谓振臂一呼,八方来从,革命队伍里难免良莠不齐,泥沙俱下。但是,漫长的革命严冬很快就来临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七一五”反革命政变接踵而至,血色恐怖中,不少投机者动摇了,软弱了,悄悄离开了革命队伍,还有的墙头草摇身一变,向昔日同志举起了屠刀……在这大浪淘沙的时代浪潮中,钱瑛始终坚持斗争、英勇无畏,以坚定的信仰在苦难中继续跋涉——
大革命失败后,她没有被敌人的屠刀杀退,反而振奋精神,坚决战斗。当时党组织打算派她到南昌参加起义,但未及起程起义就受挫。此后,她又赶赴广州,在恽代英的领导下从事兵运工作。广州起义失败,她与党失去联系,只得孤身撤出广州,经过千辛万苦、九死一生逃到香港方找到党组织。1929年至1931年她在苏联学习期间,不畏王明权威与其错误倾向开展斗争。1931年她在洪湖苏区参与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时,革命伴侣谭寿林不幸牺牲,她将巨大的悲痛化为力量,在洪湖地区与敌人展开殊死搏斗。1933年,她因叛徒出卖被捕,在狱中多次领导绝食斗争,坐牢四载仍不堕其志。出狱后,她被党委以重任,先后转战武汉、重庆、上海等地,成为党在白区斗争的重要领导人。
从这一连串奠定她党内“老大姐”地位的闪亮履历可以看出,在其革命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钱瑛始终战斗在中国革命最严酷的前沿地带,无论是武装起义、苏区创建、监狱斗争,还是隐蔽战线的长期坚持,无论是身处生死危险,还是斗争逆境,她都能保持昂扬的状态。她是直面了人生的惨烈,在枪口刀尖上摸爬滚打过来的真的猛士。在其“革命不是入股分红”理念的背后,呈现出更为深层次的信仰的力量。
“革命不是入股分红”,反映在个人生活中,就是一心为党的事业而奋斗,决不愿意为感情、为家庭而分心。这种情形在我党早期革命家身上并不罕见。1918年毛泽东曾与蔡和森、萧子升有过“为寻求救国真理,甘愿终身不娶”的约定,向警予曾发出过“终身不嫁,以身许国”的誓言;邓颖超第一次怀孕时背着周恩来偷偷做了流产手术,蔡畅在法国发现怀孕时有过准备放弃、后经母亲和李富春阻止方罢的经历……当然,这种状况存在的时间并不长,即便主张最力的向警予,也在不久后与蔡和森相恋结婚,组成了著名的“向蔡同盟”。
而钱瑛无疑是最坚决者。1929年她在苏联学习时,发现怀孕就千方百计要造成流产,并且有站到桌子上反复往下跳的举动。1931年归国时,她把女儿留在了苏联的保育院,从此天各一方,至死未见;自爱人谭寿林就义后,她就决定再不成家,彻底以身许党、以身许国。此后数十年,她只身一人,忘我工作,每日不是八小时工作制,而是包干制。1951年有个苏联专家给她做健康检查后,说她的身体大部分部件已经损伤,“寿命只有几年了,不能再工作了”。而她对此毫不在意,反而更加争分夺秒地工作。
三
革命与人性从来都不应该是对立的两面。因此,我曾一度不能接受钱瑛的这种行为,认为她的这种做法将人性的欲求压制到极限,严苛克己到不近人情。但是,在看到了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一封信后,我逐步理解了她。马克思信中有这样一句话:“对有志于社会事业的人来说,最愚蠢的事一般莫过于结婚,从而使自己受家庭和生活琐事的支配。”钱瑛就是这样的人。革命事业对于她来说,不仅是信仰,更是生活实践和生命的全部,是生死以之、死而无悔、终身崇奉的人生最高理想,故而在革命之中她是浑然忘我、全身心投入的。钱瑛在党内的地位颇高,但她说:“我才不出众,貌不惊人,我是一个极平凡的人,我唯一的愿望就是为党做一点平凡的工作。”不平凡的业绩被她表达得如此朴素,就在于她是把自己与党的事业融为一体,正如雨滴之于江水,长江之于大海。
但是,钱瑛自己过着禁欲式的清教徒生活,却没有以己及人。相反,她像大姐一样关爱着战友、下级。同志丧偶已久,她主动关心,并赠送自己的毛毯、金戒指作为结婚礼物;同志的小孩在1948年得了脑膜炎,急需住院,她亲自筹措费用,救其生命;同志在地下环境中来汇报工作,她详细安排对方利用汽车、电影院等逃避特务的追踪;同志踏上充满风险的征程,她会带他吃顿大餐,再敬上一杯葡萄酒……
因此,她也收获了同志们的衷心爱戴和情谊。这种情谊经得起任何风浪的考验。“文革”中,钱瑛被抓起来,受尽折磨,病重监外就医时,也不准亲友看望。她的战友何启君、管平、方卓芬三位女性联名上书,请求到病床前服侍她,江青生杀予夺大权在手,决不批准。钱瑛终于没见战友一面,含冤死去。而实际上,这时管平的丈夫荣高棠,方卓芬的丈夫许涤新也正被关在大牢里。在这种情况下,她们完全懂得为一个“叛徒”、“黑帮分子”请愿意味着什么。但她们仍然要求去照顾钱瑛。不是说“文化大革命”中最能看出世人的真面目吗?这就是钱瑛与战友真情的真面目。
马克思曾写道:“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在我看来,钱瑛就是这样的人。对她而言,革命是敢于豁命、至死方休的信念,是杀机暗藏、危机四伏的峻途,是艰难险阻、大智大勇的考验,是不断向前、造福众人的远景,却独独不是“入股分红”的投资。